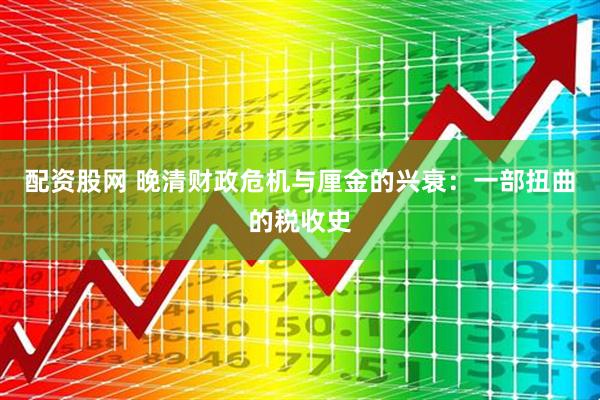
在晚清时期,有一种“苛捐杂税”存在了很长时间,它最初是一种临时筹款方式,逐渐演变成了具有全国性商税性质的一种制度,直至1931年才被裁撤,历时78年。这就是“厘金”制度。厘金的存在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多次想裁撤厘金,但是一直未能如愿。主要原因在于,厘金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并且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厘金是继田赋、盐税、关税后第四块肥肉配资股网,不是想丢就能轻易丢掉的。
一、厘金产生的原因
一般认为,晚清厘金是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军费,于咸丰三年(1853年) 八月由刑部侍郎雷以諴在扬州仙女庙附近创办的。不过目前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厘金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治理河北老河口水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后来在1840年林则徐充军新疆期间,以兴水利、行屯田为名也出现过。
据研究,厘金的最初形态是“劝捐”,也就是劝百姓捐款。这种捐款类似今天的乱收费和乱摊派。本质上,这是一种“费”而不是一种“税”。厘金由“费”变“税”是有一个过程的。这里我不打算争论它的起源问题,而是要探讨,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厘金这种怪胎。要考察此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在太平天国前夜,大清朝的财政状况。
实际上,清朝财政从乾隆中后期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除皇室供应、百官俸禄以及河工费等支出不断增加外,最主要的是军费激增。乾隆至道光时的几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竟耗费库银3亿余两。加上官员贪污盛行,鸦片泛滥,白银外流,大清朝国库日益空虚。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问题都只是清朝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一种表现,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清朝的财政体制本身具有缺陷。
咸丰以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有四大类:即田赋、盐税、关税、杂赋。其中,田赋收入约占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因此这就导致了一个很不理想的结果,即清政府财政收入被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始终无法进行突破,但是开支却日益庞大。因为田赋受到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限制。
盐税、关税,是有定额的,不能随意加征。杂赋收入虽有增加,但不足以左右财政。这种财政缺陷对清朝政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财政收入难以骤然增加。如果在承平无事的时候,这种缺陷无关痛痒,但是一遇有事,财政上就大感困难。
咸丰以前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依靠财政结余,另一种是依靠捐纳收入。财政结余不是太理想,在太平天国爆发前夕,也就是道光30年(1850年),户部实存银187万余两,加上各省起解在途225万余两,也就412万余两,这些钱对于帝国的正常运转已经是捉襟见肘,想镇压太平天国,这点钱塞牙缝都不够。
另一种方法就是捐纳。所谓捐纳,说直白点,就是花钱买官。这种方式起于汉文帝“纳粟拜爵”,后被历朝政府所采纳。到了清朝,每有大事件,就盛行捐纳,补助财政。但是纵观历史,没有哪个朝代像清朝这样热衷捐纳的。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清政府首先采取推广捐纳的老办法,以此向社会各阶层筹集军饷。从1851年至1852年年底,捐纳收入约有300万两。可是到1853年,只收得67万两,原因是这几年该捐纳能捐纳的全都捐了,连三岁小孩都买了功名。导致捐纳者一时间甚至都绝迹了。由此可见,推广捐纳方法已成为强弩之末,清政府难以依靠捐纳收入来解决财政困难。
1851年1月,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廷针对南方各省镇压太平天国拨款一千多万两白银,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例如咸丰二年(1852年)户部银库收入万836.1万两,支出为1026.8万两;咸丰三年(1853年)收入为444.3万两,支出却达847.1万两,以至于无法按时、足额发放兵饷,如果财政再这样恶化下去,不需要太平天国进攻,自己就要崩溃了。因此,清政府必须想办法寻找新的税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厘金产生了。
二、厘金的危害
厘金在全国推广后极大地缓解了地方的财政困难,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军饷不足的燃眉之急,也帮助清政府暂时度过了政治军事危机。但是厘金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厘金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分割了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是维系整个社会生产的纽带,商品流通的时间越短,再生产周期也就越快,取得的经济效果也就越大;反之,经济效果就越小。这一经济规律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任何时期和朝代。但在清朝后期政府推行的商业税——厘金,却逆此规律而行,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
首先,厘金局卡林立,官员重重盘剥,增多了流通环节,限制了商品的流通速度。厘金自创立后,迅速得到推广,各地关卡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其中不乏私设、滥设的关卡。据估计,到清末时期一切属于厘金局之类的关卡,全国就有12000余个。
其次,厘税过重,重复征收,提高了商品成本和价格,大大降低了商品的流通量和购买量。厘金推行的是“任人不任法”的原则,所以从一开始,它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而是地方各自为政,自定章程,中央对地方的厘金征收不加过问,致使各地税率很不一致,并且有越来越高的趋势。最初厘金税率1%,但是到后来有的地方甚至高达20%。
由于厘金是一种交易税、商品通过税,所以此种巨额税负全部转入到了商品本身中,必然提高商品的成本和销售价格,最终在交易中又转嫁给了消费者。这就使早已贫困交加的中国人民的购买力变得更低。由此可见,厘金已经导致“百货滞销,四民俱困”。
再次,厘金制的推行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商品流通和商业的发展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而市场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物畅其流。但清王朝非但没有减轻国内关税以促进商品流通,反而推行厘金这种严重制约商品流通的税制,严重阻塞了长距离贩运贸易的途径,也加重了长距离贩运贸易的成本,从而人为地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封锁,分割了国内市场,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发育。
二是扼杀民族工商业发展,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倾销大开方便之门。与晚清政府处于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发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往往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一般对于有损本国产业发展的进口商品加大征税力度,而对本国的制成品不征或轻征出口税。但是,清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列强的强迫下它同意了“协定关税”,降低了洋货的进口税率。这本来已对国内产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厘金税制的创立又极大地加剧了这种危害:一方面,厘金的征收加重了中国产品的价格,不利于本国产品的出口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洋商货物除纳5%的关税及2.5%的子口税外,即可畅行天下,不再抽征,其价廉物美的优势更多一层,几乎是处于倾销的状态。这种在中国领土上只征诸华商、不征洋商,只征国货、不征洋货的厘金制度,使中国商品在与洋货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使商业利润多归洋人。在这种不公平的条件下,对于艰难起步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是严重的摧残。
三是厘金成为地方拥兵自重的经济基础。厘金害商病民如此,清政府并非全然不知,力图加以改变,然而之所以多次议而不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财政极度困难。曾国藩、郭嵩焘、胡林翼等人主张保留厘金制度,无不以筹措军饷为由。事实也确实如此。清政府只好认可地方督抚继续借助厘金制度自行筹饷,除一部分收入上缴中央外,很大部分留作地方开支,这导致晚清中央财权下移,表明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开始失控,地方督抚因此可凭借其地方财力拥兵自重,形成兵为将有的格局。国家调派地方军队,“一兵一卒一饷一糈,朝廷皆拱手待之督抚”,地方督抚俨然手握军权财权。军权与财权一旦由地方督抚所拥有,中央政府就不可能有效地对地方行使控制权,致使中央政府的号令在地方不能得到切实的贯彻。此后在辛亥革命中,清政府就在地方各省纷纷独立的态势中垮台。
按民国的财政体制,厘金收入虽然归中央政府,但在军阀混战时期,因各地军阀具有对厘金的充分管辖权,厘金实际上仍然是地方的一项重要财源。1928年中央势力范围内的军费已达5700多万元,若包括地方军阀的军费,则需6.6亿元。庞大的军费支出,只能在各地自筹,而厘金收入显然是地方军阀筹集军费的主要来源。地方军阀凭借厘金收入供养、扩充自己的军队,上抗中央,下欺百姓,混乱不止。其结果,国家政权日趋削弱,政令不出都门,政权朝不保夕。厘金已成为地方拥兵自重的经济基础。
三、厘金的裁撤
厘金制度对晚清社会经济的严重危害引起了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的强烈不满,要求裁撤厘金的呼声不绝于耳。裁厘要求最为迫切的当然是直接受到厘金剥削的工商业者、农民、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他们的声音对清政府来说很微弱,所以他们往往采取歇工、罢市、闹局、毁卡、殴打官员等更为激进的方式。
资产阶级改良派是新兴工商业的代言人,因此,其代表人物马建忠、陈炽、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纷纷提出了废除厘金,振兴民族工商业的主张。他们无不对厘金病商殃民、损害国家利权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谴责。
各阶层人民的“裁厘”呼声这么大,但是一直未见效果,根本原因是厘金极大地缓解了中央的财政危机,同时,还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这就使得中央与地方谁都无法断然放弃厘金。例如,宣统三年(1911年)厘金收入达4318万余两,是清朝政府预算总收入的14%,只能说这块肥肉太诱人了。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29-1930年间,裁厘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迫于形势的压力,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裁厘通电:“对于全国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为统税、统捐、专税、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及正杂各税捐中之含有厘金性质者配资股网,又海关之50里外常关税及其他内陆税,陆路边境所征国境进口税除外,子口税、复进税等,均应于本年12月31日止,一律永远废除。”至此,厘金制度最终废除。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一鼎盈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